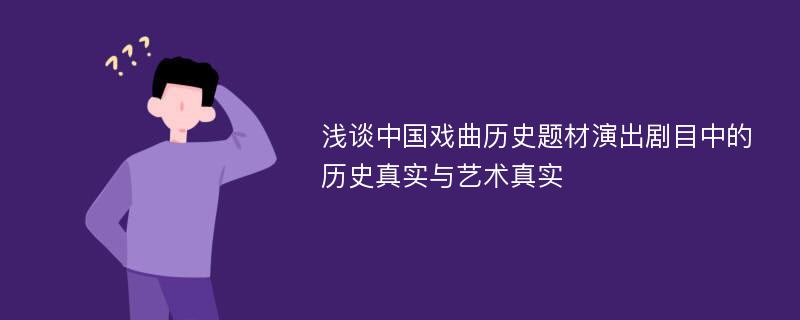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J7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12-092-02
2008年,在河南省第十一届戏剧大赛上,河南省豫剧二团推出了一部新编历史剧《台北知府》。据说,这部戏因为与史实有较大出入,所以受到了不少专家的批评。专家难道不知道这是在演戏么,真实的人物加上虚构的事件在艺术创作中也是允许的。然而,考虑到这部戏以后要到祖国的宝岛台湾去演出,台湾观众欣赏的习惯是戏曲必须反映真实的历史事件,如果是虚构的,那么将会被禁演或者被起诉。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加关注到了一个长期以来戏曲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要历史真实还是要艺术真实?
中国戏曲历史题材演出剧目一般都是根据已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也有根据真人虚构的假事创作出来的剧目,还有根据真事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安在他人头上创作出来的剧目,更有的是仅凭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通过虚构的人物虚构的事件就创作出来了剧目。在这里就要牵扯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认识体现在这类剧目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我国戏剧界自上世纪五十年末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戏既是历史题材,那么,“一史一事,均有出处”。写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人物,在具体的描绘中就必须有特定的历史事实本身的制约,既不容编造,也不容篡改。——如果这样看待历史的真实性,恐怕戏曲中许多传统剧目都是反历史的。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郑州市实验豫剧团推出了一部新编历史剧《程咬金照镜子》,这部戏就是写了作为农民起义首领的程咬金在投靠大唐封为王侯之后蜕变沉沦。他厌烦了从农村来京寻找他的结发之妻,在见到年轻貌美的女子之后,听信麻参军之言抢到另建的豪宅之中再次成亲,不料花轿抬来的却是丑陋的大脚夫人。这部戏当年的剧场效果是很火暴的,一连演出一个月还难以满足观众的需求,被拍成电影后更是风靡全国。但,在火暴的背后,却传来专家们不同的声音,甚至是质问。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程咬金真的就是这样的么?有历史根据么?并且这也与以往程咬金的形象大相径庭。再譬如,新乡市豫剧团推出的《琵琶记》中讲述的蔡伯邕与赵五娘的动人故事,不知道赚足了多少观众的眼泪与感叹,其实历史上哪有这些人和这些事啊?用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戏剧情节编演的《捉放曹》,把曹操刻画得活灵活现,可是翻阅一部《三国志》也找不到这段历史事件的记载。三国的史书上对于貂蝉的记载是很少的,可是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那就太丰富了,如《关公与貂蝉》、《吕布戏貂蝉》等。总之,以严格的历史真实性去检验这些剧目,它们都会因给人民认识历史造成混乱,连存在的权利都会被剥夺。戏曲观众可能会问,为什么独独在戏曲艺术这块土壤中,能够生长出如此之多的“移花接木”之树,并结出“荒谬”之果?
一般来讲,戏曲历史题材的传统剧目,并不是由作家直接取材于史料编写成戏曲文学剧本的,而是根据小说、民间传说、说唱故事改编过来的。比如包公戏《小包公》《下陈州》《包青天》《包公三堪蝴蝶梦》《探阴山》《斩包公》《包公辞朝》《包公坐监》《包公戏娘娘》,杨家戏《佘洪招亲》、《令公归宋》《血战金沙滩》《杨门女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破洪州》《穆桂英挂帅》《五世请缨》等。这些戏的取材早已被演义化和说唱化了,这个“演义化”和“说唱化”,正是从前民间戏曲的史剧创作有别于今天的作者直接从事史剧创作的特殊点。史料在社会上“演义化”、“说唱化”的过程中,就已经渗入了大量的艺术虚构和加工。由于当时的人们和艺人文化水平低下,缺乏历史知识,更谈不上全面占有材料,所以对史料和前人所提供的东西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歪曲:或是把这个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情,移到另一个人物身上;或是把某个朝代发生的事件与另一个时代相互替换。这样,小说里和戏曲舞台上所描绘的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自然与史料所记载的相距甚远,以致根本就对不上号。如:诸葛亮、包拯、杨继业、潘仁美、王昭君等,这些鲜明生动的戏曲人物形象,他们就都与真实的历史有较大的出入,甚至与史实完全相反。这种漫长曲折的由史书进入民间、由民间进行艺术的加工,再一代又一代的流传衍变,致使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与历史事件的原本状况日渐淡化、湮灭、消失的情况,在我国民间文学和民间戏曲中,俯拾即是。
中国戏曲历史题材演出剧目中的这种现象该怎样解释呢?马克思曾指出: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戏剧家,“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艺术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这种“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和适合于普遍使用的艺术形式。可见,民间对史料采取了“不正确理解的形式”,绝非是胡编乱造,也不是无目的的随意摆弄历史。他们是按照人物典型化与题材戏剧化的基本准则,进行着合乎戏曲创作规律的增删取舍。同时,每个时代的编演者还要把自己的生活愿望、思想感情、善恶观念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丰富、融合进去,对历史人物赋予自己的理解。经过这样一番创造性加工,一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演化为戏剧冲突和戏剧人物,消退了原有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里,所谓由历史人物向向戏剧人物的演化,其实质就是人物远离了历史的原型,而取得了戏剧的属性。
正是由于一部分戏曲剧作家为了追求剧本创作中历史的真实,他们根据历史人物所作的真实事件重新写出一部分新的作品。比如,我国绝大多数剧中都有的一个演出剧目《秦香莲》(也叫《包青天》),这部戏的却是把清朝的人物写到了宋朝,陈世美也并没有做过什么杀妻灭子的罪行。为此,四川省广元市豫剧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推出了《陈世美喊冤》一剧,可以说这部戏就是为陈世美在翻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戏曲界刮起了“翻案戏”之风。然而,这些“翻案戏”总是演不过那些“历史不真实的戏”。由此,我认为中国戏曲历史题材演出剧目还是要遵从艺术真实大于历史真实的创作原则吧。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剧场中或者电视机前坐的观众,特别要提的是那些中老年人,他们绝大多数认得字,也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更不要说那些青年人和大学生们了。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是在看戏,是在欣赏其中的艺术,不是在看历史故事。他们明明知道曹操不是什么大奸臣,而是一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但还是津津有味地在看《群英会》《击鼓骂曹》《斩关羽》《曹操与关公》《曹氏父子》《曹操与杨修》等戏,看过之后他们还要在对剧中的曹操品头论足。这种现象也就更有力地证明了艺术真实的无穷魅力。
现在,我们的剧作家和艺术家们也是在与时俱进,在重视艺术真实的前提下,也尽量地给历史真实以关照。比如,著名青年剧作家陈涌泉根据《赵氏孤儿》创作的《程婴救孤》,由河南省豫剧二团推出后,先演红了郑州,再演红中原,然后是全国,接着港澳台和欧洲。当然这出戏的成功最离不开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的表演艺术带来的巨大魅力。因为京剧演出版本的《赵氏孤儿》在全国有着深厚的观众基础,豫剧要想打造成功困难是很大的。其中很关键的就是编导演们紧紧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地结合了在一起,通过历史的真实感传达出了艺术的真实感。中国豫剧的早期剧作家樊粹庭根据传说创作出了《涤耻血》,樊戏和陈派的研究专家石磊又根据此剧加上查看历史记载重新创作的《大宋英烈》也是很好的例证。
时代在变,那么我们这些梨园行的编导演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进行艺术创造。特别是针对中国戏曲历史题材演出剧目的打造上,还是力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合理结合为标准吧!
